作者簡介:芝麻开门,古董臺灣網網站站長,愛好古董古玩收藏,尤擅長古錢幣類鑒定。
玉石、陶器、青銅、竹簡、帛畫、石雕、敦煌壁畫、山水畫……蔣勳在這些被“美”層層包裹著的藝術作品中,開始逐漸思考起它們形式的意義。
繪畫的卷收形式和空間長度有關,和繪畫背後的美學主張也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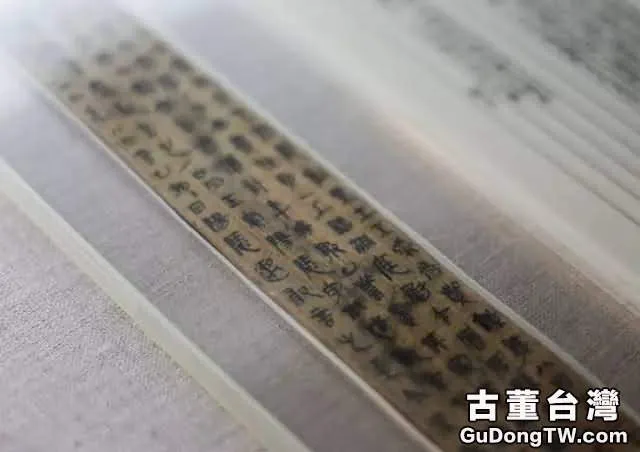
-裡耶秦簡-
立軸形式的繪畫,懸吊在牆壁上,是一個完整的繪畫空間,但是,在收卷和展放時繪畫空間的改變,是西方硬框式繪畫所沒有的。這種繪畫空間的卷收與展放,一般人只是從收藏的方便來思考,事實上,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中國時間與空間觀念的反映,一種延續的、展開的、無限的、流動的時空觀念,處處主宰著藝術形式最後形成的面貌。
這種延續的、展開的無限流動的觀念,在長卷形式的繪畫中表現得就更為明顯。
長卷的繪畫形式應該成形於早期的竹簡,以韋編竹,連貫成卷,是中國展開與卷收形式的較早來源。

-銀雀山漢墓竹簡-
東漢和林格爾墓葬中的壁畫,由於描寫墓葬主人的一生,有連續展開性的格局,但是因為是壁畫,只是長條形的固定格式而已。
顧愷之的《女史箴圖》,《洛神賦圖卷》,《列女傳圖卷》,雖然都是摹本,依然保留了當時長卷的繪畫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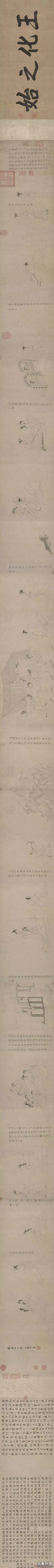
-女史箴圖卷-
《女史箴》與《列女傳圖卷》是故事性的分段連環圖形式,每一段旁有文字說明,結構上雖然有呼應,但是獨立性很高。

-列女仁智圖卷(宋摹)-
《洛神賦》的連續性非常強,山水在人物運動的關係間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曹植與洛神對望,中間隔著大段的山水,比例上恰恰是前一組人物實體在“虛”上的對照,而背景內翔遠而去的龍鳥則展開了第三度空間的遼闊性。這件宋摹本如果忠實保留了原作的構圖佈局,那麼在晉代,從連環圖式的長卷轉變為真正具有連接呼應作用的長卷,顧愷之應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洛神賦圖卷-
稍後於顧愷之,北方從印度傳來的宗教變相圖,更加強了中國長卷性繪畫的發展。
敦煌二五七窟北魏的《鹿王本生變相圖》是“北魏本生故事畫中最早的橫捲連環畫之一”。這件壁畫的構圖形式非常特別,“故事情節從兩端向中間發展形成高潮而結束”。中國本土的長卷,幾乎一律是由右向左發展,視覺開始於右端,結束於左端。在這由右向左發展的空間中,畫家自然必須考慮到卷軸展開的速度與方向。中國的長卷畫,從來不是完全攤開來陳列的。也就是說,觀賞者與長卷的內容,不會在同一個時間內做完全的接觸。在畫卷展開的過程中,觀賞者一面展放左手的畫卷,一面收卷右手的起始部分。右手收捲著過去的視覺,左手展放著未來。在收卷與展放之間,停留在我們視覺前的約莫是一公尺左右的長度,等於兩手張開的距離罷。這大約一公尺左右的長度,在與我們視覺接觸過程中,有千萬種不同的變化,它分分秒秒在移動,和前後發生著組合上的各種新的可能。

-鹿王本生變相圖-
韓混《五牛圖》,看來各自獨立,但是行進的變化頗有趣。一開始是遵循由右向左的方向緩緩進行,到了中央第三頭牛,忽然成為正面,行進的方向與速度都中止了,彷彿向畫面外的觀賞者一照面,畫面獨立成靜止的鏡框式的舞台。然後,到第四頭牛,一方面保持原有行進的方向,繼續由右向左發展,另一方面卻利用牛的回頭,造成一個轉折的空間,經過這一轉折,才又恢復結尾第五頭牛繼續由右向左的暗示。

-五牛圖-
以敦煌的資料來看,佛教故事畫影響出來的變相圖對中國長卷形式繪畫的完成有莫大助力。第二九六窟,北周《五百賊歸佛因緣》,長427厘米,高46厘米;北週二九O窟的《佛傳圖》長432.5厘米,高82厘米,而這82厘米中又橫剖為三段,所以實際上的長度應是432.5厘米的三倍長。北週四二八窟的《薩堙那太子捨身飼虎》長417厘米,高64厘米。有名的晚唐一五六窟壁畫《張議潮出行圖》及《宋國河內郡宋氏夫人出行圖》,均長達855厘米。

-五百賊歸佛因緣-

-五百賊歸佛因緣二-

-五百賊歸佛因緣三-

-五百賊歸佛因緣四-

-張議潮出行圖-

-張議潮出行圖二-

-張議潮出行圖三-

-張議潮出行圖四-
這些佛教的故事經變圖,與中國的長卷形式是一齊發展起來的,但是,壁畫受制於建築空間,自然在時空的轉換上不及紙帛類可以卷收與展放的長卷繪畫。
推測為南宋人摹本的五代南唐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在長卷繪畫的結構上是值得注意的傑作。全卷長333.5厘米,高28.7厘米。在333.5厘米的長度中,分為五個段落,每一段落約長60厘米。





在第一段中,以床榻為起始。床只露一角,在畫卷右上方,被褥不整,床上置一琵琶,拉開了夜宴的序幕。
因為床只露一角,不刻意把這個“開始”當一個獨立的部分來看待,似乎是一個無限時間中偶然被截出來的一個段落。

畫卷展開,隨著最右方榻上的主人韓熙載及狀元郎粲,及榻邊侍女,三人視線重複的暗示,使畫卷有急速展開的慾望。越過擺滿果點的几案,畫卷下方的賓客,仍和開始的三個人保持同一視線,加強由右向左的行進方向。但是,畫捲上方的教坊副使李家明,雙手按拍而合,身體已轉向正面,使行進的速度發生變化。經過這一停頓,左邊再次出現的是一組五個人物,幾乎是兩條平行線,身體一律朝向右方,與卷首的韓熙載、郎粲呼應。但是,他們的面部仍然轉向左方,重複地把視線的行進方向落在這一段的焦點人物——彈琵琶的女子身上,女子背後是一面大的立屏,立屏後露出半身的女子,在嘹看全場,第一段落在這屏後人物的嘹看中結束。
第一段,從床榻開始到立屏結束,巧妙地用了大型的物件做畫面場景的分割。這一段,可以做一幅獨立的繪畫欣賞,但是,又必須加入到整個長卷的發展中去。獨立來看,類似西方繪畫的觀察,畫面以李家明為視覺中點,視線的焦點集中在畫面左下方彈琵琶的女子身上。

若以中國長卷的結構來分析,在這暫時使人停止流連的靜止畫面中,時間向前的暗示仍在進行,右手要卷收,左手要展放,一切的美景、人物、聲色之好,一切暫時的棲止、眷戀,都不能違反那“逝者如斯”的時間的進程。
在卷收與展放中,有對逝去的不捨留連,有對新展現事物的欣喜驚訝,時間流逝的觀念,繁華與幻滅的對置,便在這長卷形式中一一深人中國人的生命之中了。
《夜宴圖》的第二段,隔著立屏,是另一個場景。韓熙載換了輕便的服裝,手持鼓錘,正在擊打一面紅漆如桶的羯鼓,配合著左方名妓王屋山的六麼舞。

這一段畫面上的八個人物,圍繞著擊鼓和舞蹈的故事中心,仍然以身體和視線的方向,暗示著行進的內在時間。惟一的例外是僧德明,他一身和尚打扮,背向王屋山的舞蹈,視線又不在韓熙載的擊鼓上,他陷入沉思冥想之中,彷彿與四周的聲色無關,使畫卷的行進節奏發生了阻礙,是對生命更深的冥想,忽然置身於時間與空間之外。
在一般習慣的二段與三段之間,並沒有類似立屏隔開的做法。那面向右邊拍手擊節的女子似乎是二段的結尾,用身體的朝向來間隔。
接下來,到手捧溫酒杯盤的侍女出現,進入第三段落。巧妙的是,這二段到三段之間,只是空白。空白成為中國長卷繪畫精彩的部分,這“空白”並不是“沒有”,它是老莊思想“無用之用”一脈相承的嫡裔,它是對時間與空間更深刻的思考,宋元以後,在中國藝術中發生了莫大的影響。

《夜宴圖》第二段到第三段的轉換,不借助任何實物的間隔,這種空白的應用,提醒了我們,在真正的時間之中,並沒有段落,床榻與立屏都是假相,我們常用的秒、分、時、日、月、年、世紀,也都是假相。時間本身,是一個汨汨無止境的流逝過程罷。這種時間與空間的轉換,在此後山水畫中發展得更為巧妙,在中國新起的舞台藝術、園林藝術、章回小說中也在在找得到例證。
《夜宴圖》第三段從捧溫酒杯盤的侍女開始,彈琵琶的女子掮著琵琶由右向左行走。彈琵琶的女子在第一段是視點中心,在第三段,曲終人散,跳過第二段,接到第一段,時間被錯置了。十分具象徵性的床榻再次出現,仍然是被褥不整,好像這緩緩走來的女子正準備著把琵琶橫置床上,這個符號,使我們想起卷首的床榻與琵琶,當同一個形象第二次出現,便有了象徵的意義,而最有趣的是,在時間上,是與我們邏輯的理解相倒置的。這種時間疊壓,前後錯置的感受,更接近我們真正的意識狀態,是長卷繪畫逐漸形成的一大特色。
原來,連由右向左一直線的時間方向,也是假設而已。在卷收的過程中,時間在同一個軸心上竟然不斷疊壓重複,形成一個不斷循環的無數圓。在圓形上,既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或者說,在圓上,每一點都可以是開始,也可以是結束。
韓熙載坐在榻上,重新披上衣服,似乎剛擊完鼓,正在洗手,五位侍女在側環繞。他面朝右上,與第二段正在擊鼓的韓熙載面面相覷,似乎在一剎那間,忽然看見了另一個自己,時空的限制完全被破壞了,人可以出入於任何時間與空間之中,無有阻礙。中國的長卷繪畫發展至此,連強硬的劃分第二段與第三段也只是討論上的不得已,真正長卷繪畫企圖達成的時空正是一個渾然不可分的時空,企圖把我們從假相的、被分割的時間與空間中救拔出來,達於真正自由逍遙之境。莊子《齊物論》中提出的“不知周之夢為胡蝶歟?胡蝶之夢為周歟?”

正是這種時空觀在中國藝術上大放異彩的先聲罷!
利用床榻做間隔,進入第四段,韓熙載卸去了外衣,袒腹而坐,一手揮扇,畫面正中央是五位弄笛吹簫的女子,李家明執檀板合拍。五位女子三人面朝右,二人面向左,三二錯置,使畫面造成扇形張開的形式,使觀賞者視覺固定靜止,是正面視覺的焦點。左右兩側則由李家明與韓熙載互相呼應,構成一個可以獨立的段落。

李家明後又張一立屏,屏側一男子身體朝向右方,是屬於第四段場景中的人物,但是他頭又轉向左方,預告了第五段的開始。這是長卷繪畫中轉換時空的手法,這種角色十分接近傳統戲劇中的“撿場”,他們似乎與主題無關,面無表情地走出來,又像是時間本身,收拾殘局,為下一個場景佈置新的空間。

第五段是一個結尾,七個人物中六個朝向右邊,是與長卷由右向左完全相反的行進方向。他們似乎被屏側的男子宣告要出場,屏側女子用手勢招喚,韓熙載手執鼓錘出來,後面跟著有點害羞、舉袖掩口,被人力邀而出的名妓王屋山。

這結尾是夜宴的高潮,卻又似乎那麼不願結束,用反方向的進行,把結尾轉成開始。形象上,這一段又似乎是第二段韓熙載擊鼓、王屋山舞蹈之前。
這樣的結尾,便造成了一個不僅錯綜複雜,而且銜接卷首的循環往復的時間暗示,是週而復始的“圓”,是易經“始干而終未濟”的觀念,是熊十力先生解釋《禮記·天道》時說的:“天道之運,新新而不守其故。才起便滅,方始即成終。才滅便起,方終即成始。始無端而終無盡。”
起滅終始在一點上,起滅終始也可以無限。在直線上是無法無限的,必有兩端。“無端”的時空恰好是可以卷收與展放的長卷。
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說山水畫要“鋪舒為宏圖而無餘,消縮為小景而不少”。長卷繪畫對中國時間與空間的表現要到宋以後的山水畫中更形成熟,發展到了高峰。
